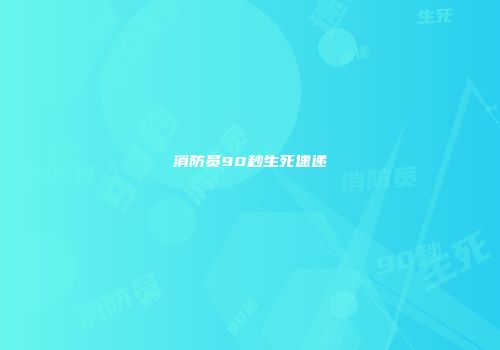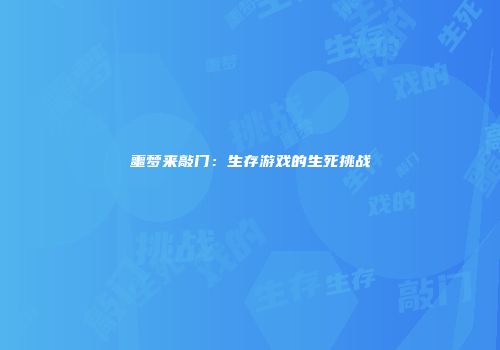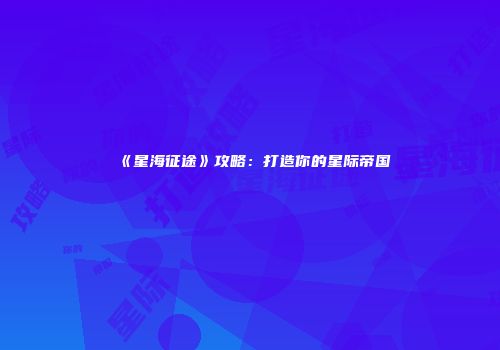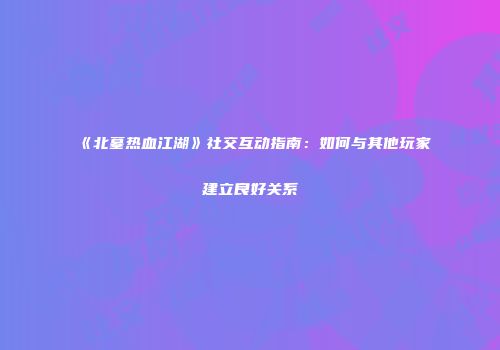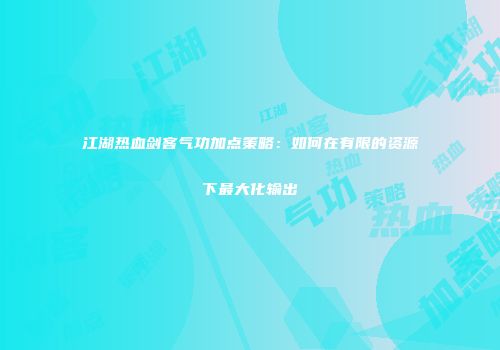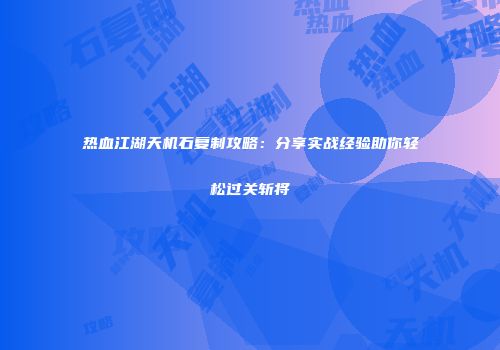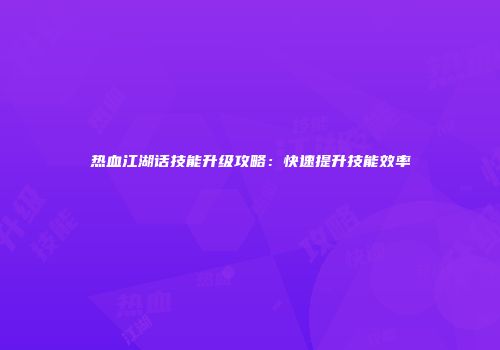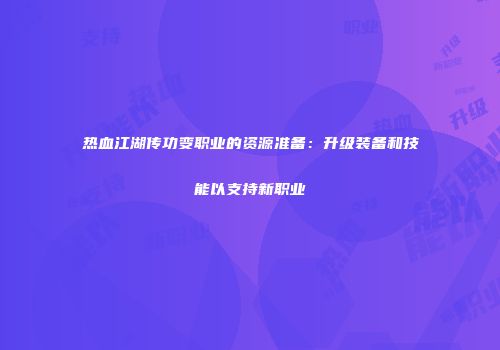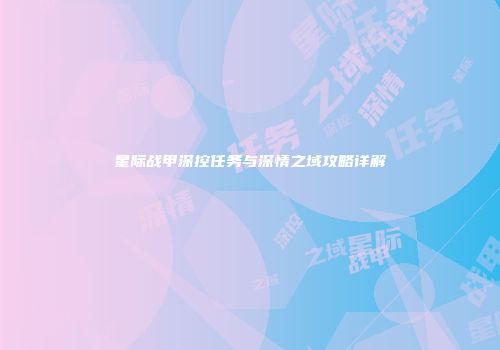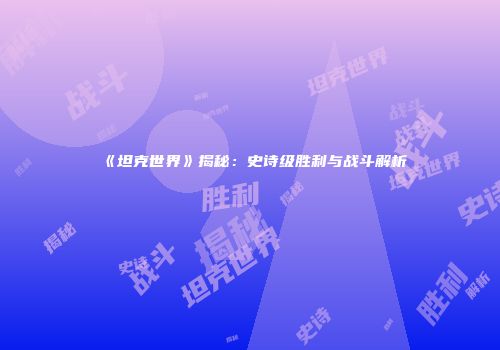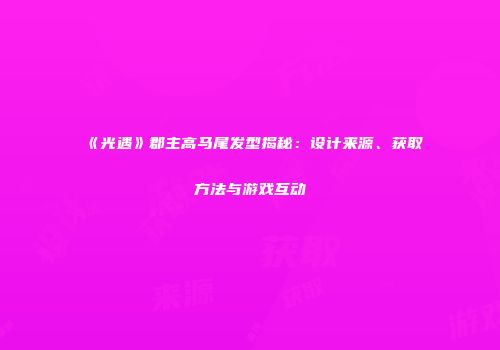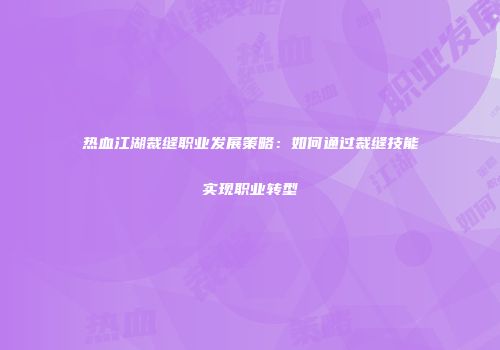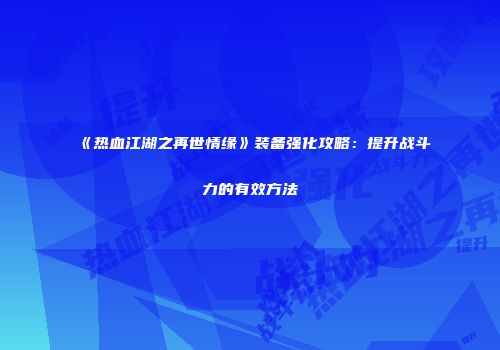消防员90秒生死速递
 2025-09-03 14:47:54
2025-09-03 14:47:54
当警铃响起时
凌晨三点,我刚把热好的夜宵端上桌,警报器突然像被踩到尾巴的猫似的尖叫起来。手指比大脑更快做出反应——抓起头盔往外冲时,微波炉还在发出"叮"的完成提示音。这场景我经历过两百三十七次,但每次听见警铃,心脏还是会像刚跑完负重十公里那样狂跳。
出发前的90秒黄金准备
- 检查装备就像检查呼吸:空气呼吸器的压力表必须稳定在300bar,面罩密封测试时会发出"嘶"的漏气声——这声音比任何安眠曲都让我安心
- 防火服的每个褶皱都要抚平:上次老张因为裤脚卡了个小石子,结果烫出个硬币大的水泡
- 把对讲机调到三频道时,手心在微微发汗——这是新来的通讯员小王第一次跟现场
燃烧的迷宫里找生路
隔着两条街就看见浓烟像条黑龙直窜夜空,火光照得整片居民楼忽明忽暗。三单元四楼那户的防盗窗已经烧得通红,像烤箱里的铁丝网。我能感觉到面罩开始发烫,这不是好兆头。
| 危险信号 | 应对策略 |
| 玻璃爆裂声 | 立即寻找承重墙掩护 |
| 黑色浓烟转灰白 | 准备应对闪燃现象 |
| 地面温度超过120℃ | 必须采取跪姿前进 |
热成像仪里的生命迹象
当屏幕上的橙块开始闪烁时,我的呼吸突然变得很轻——那是卫生间角落蜷缩着的人形轮廓。隔着三层砖墙,我仿佛能听见被困者艰难的咳嗽声。热浪让仪器边缘的成像有些扭曲,但那个微微起伏的胸腔轮廓清晰得刺眼。
破拆的艺术
液压剪咬住防盗窗的瞬间,火星像除夕夜的烟花四处飞溅。金属断裂的"吱呀"声让我想起小时候掰断铅笔的声响,只不过现在手里握着的是能承受20吨压力的救援器械。
- 45度角切入窗框最脆弱处
- 注意保留逃生通道支撑结构
- 随时用水流为切割点降温
当终于把人从废墟里抱出来时,我才发现防护手套的掌心部位已经被金属毛刺划开了口子。怀里的老太太轻得像是被火苗舔过的枯叶,但她的手指还紧紧攥着个烧变形的相框。
撤退时的生死时速
返程时楼梯间突然传来玻璃炸裂的脆响,这是我最不想听到的"礼花弹"。后背能清晰感受到火浪推过来的力度,就像有双滚烫的手在使劲推搡。数着台阶往下冲时,突然想起训练手册第47页用红笔划的重点:"撤退路线永远要比进攻路线短"。
黎明前的交接
把伤者交给医护人员后,我靠在消防车上啃早已凉透的包子。东方泛起鱼肚白,火场飘出的青烟在晨光里袅袅上升。对讲机里传来指挥中心确认全员归队的呼叫,我数了数车库里亮着的顶灯——二十三个,一个不少。
裤袋里的手机震动起来,是妻子发来的消息:"早餐在锅里热着"。抬头看见二楼住户的窗帘轻轻晃动,不知道是谁家的小孩躲在后面偷看我们收拾器材。晨风裹着焦糊味掠过鼻尖,新来的小王正在给云梯车系防雨布,他打绳结的手法还有点笨拙,但已经比三天前好多了。